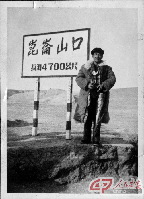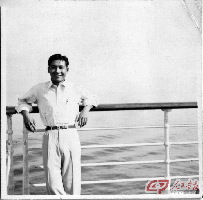周镜院士:给岩土“把脉”的人

从大西北的荒漠到大西南的山区,长长的铁道旁有无数他留下的足迹。从北方的港口到南方的机场,也都有他为复杂的岩土工程问题“把脉”的身影。
他叫周镜,今年88岁,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岩土工程专家。他长年奔波在祖国各地,在路基工程出现问题的地方,给造成工程病害的岩土“看病”并制定“手术方案”,为修建四通八达的铁路、港口、机场打下坚实的路基。
炎热的七月,88岁的周镜在他工作了60多年的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铁道建筑研究所接受本刊记者专访。白色短袖衬衫、藏青色裤子、黑皮鞋,他一身朴实的打扮,脸上写着岁月的痕迹,但依然清秀,眼睛虽不大,但很有神,说起话来温和慈祥,平易近人。
虽然获得过不少国家级嘉奖,但周镜对自己最喜欢用的评价是“一般”、“普通”。当年,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他毫不犹豫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回国终日与泥土相伴,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这种朴素的爱国观并不是某一个人独有,而是我们那一代人绝大部分共有的思想:国家不强盛,就会挨欺负。”
留美归来的“土专家”
1950年冬天,25岁的周镜来到位于唐山的铁道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前身)土木研究组工作,任助理研究员。他和同事们住在泥顶土墙的平房里,室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卫生间,房间的北墙上结着一层冰,整个冬天没有融化,只有靠近南墙的火炉能去除些许寒意。
那时,周镜刚从美国回国。他在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考试获得购买官价外汇自费留学美国的资格,1949年春在俄亥俄州大学土木系获硕士学位,后来在俄亥俄州公路局材料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他是从报纸上得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1950年,听闻英国政府允许中国留学生坐船经香港回国,他立刻递交了申请。同年8月,他从旧金山登上归国的轮船,与他同船的有100多名中国留美学生,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后来的多位院士。
在美国,周镜已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回国后,生活和科研条件落差很大,但他既无怨言,更不后悔。
他回忆说,自己出生和成长在中国最动荡的年月,从小切身感受到,一个民族若不能自强自立,就会遭受外强欺侮。小时候,为躲避战乱,他跟随父亲曾辗转于江西、江苏、湖北、湖南等多地。后来,去美国留学,虽身在当时相对开明的北方州,但他仍然明显感受到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偏见。他还记得当时流传的顺口溜:“白人永远正确,黑人靠后站,有色人种在边上等等。(White are right. Black get back. Brown stick around.)”
“只有祖国强盛壮大,华夏子孙才能扬眉吐气,不然,永远被人看不起,在国外也永远是二等公民,不可能真正融入那个社会。”怀着这样的想法,周镜当年决定回国时,没有丝毫犹豫。后来得知,经香港回国的轮船仅开行三四个航班就停止了,美国颁布了禁止中国留美学生出境的法案,他感到自己很幸运。
回国之初,历经长年战乱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作为留美归国的人才,周镜可以有很多的就业选择,但他既没有继续自己在美国时从事的公路研究,也没有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是来到位于唐山的铁道研究所,与同样刚回国不久、毕业于麻省理工的卢肇钧一起筹建土工试验室。周镜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铁路比公路更有发展,而且土力学当时在国际上也是一门刚兴起的学科,土工试验室“很有前途”。
周镜眼里这个“很有前途”的试验室建在一个仓库里。经费捉襟见肘,采购量筒、烧杯等最基本的试验器皿时,一次只能买一个,其他设备能自己动手做的就绝不花钱买,比如捡来废旧钢轨加工成固结仪的加载架。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卢肇钧的带领下,周镜和同事们一起筹建起了中国铁路系统第一个土工试验室(也是当时全国少数几个最早的土工试验室之一),并编写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土工试验规程》。
“好像完全没有去考虑物质、生活条件这些东西。当时,我们国家就是那个情况,而且我小时候家里的生活也没多好,所以,觉得那样的生活是很自然的事。”周镜说。
他特别提到“榜样的力量”。当时,铁道研究所的不少领导都是比他更早、20世纪30年代留美归国的,他们全都不辞辛劳、不畏艰难、勤勤恳恳地工作,没人计较过物质条件。
为了修建穿越沙漠的包兰铁路,副所长翁元庆带着两位同事,骑着骆驼,自带炊具和干粮,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中一个已荒芜的小土地庙里住下来,观测沙丘的移动规律,做固沙实验,为中国沙漠筑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一次,周镜和铁道研究所首任所长许鉴一同出差,需在西安转车,但由于火车晚点,到达西安时已过子夜,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叫“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全是土炕通铺,铺上已经睡满了人。店伙计关照,找没人的空位爬上去,睡觉时记得把鞋子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不然鞋被别人穿走了概不负责。周镜平生第一次走进这种客店,还在站着张望时,只见许所长二话没说,已经爬上炕睡下了。
“在北美西部一些大宾馆的大厅里,陈列着当年西部开拓者用过的大篷车。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港口,矗立着他们的祖先身带镣铐的塑像。美好的现在是祖先用血汗铸造的。要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现状,需要几代人去努力,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周镜说,“当年回国,我并没有多崇高的世界观,想法很简单,就是感觉新中国有希望,想回来参加建设。”
1952年,周镜随铁道研究所土木组从唐山搬迁至北京。在一块当年满是麦田和坟地的土地上,全新的铁道科学研究院一点一滴地建设起来,周镜也参与了建院工作。
若不热爱工作,不可能干得好
建国初期,中国铁路建设的重点在西北,西北地区有大面积黄土高原,而国内在黄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近乎空白,唯一可参考的依据是苏联的有关规范,照搬此规范进行铁路设计和建设,筑路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边坡坍塌等问题。为此,1956年,周镜带队,与唐山铁道学院的老师、第一勘测设计院的工程师们一起,在西北地区的陕甘晋豫四省开展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黄土工程调查。
他们沿着铁道从天水到兰州徒步考察,背着干粮和行李,饿了就啃糜子面的窝窝头,累了就近找一个养路工区住下,睡自带的行军床。那时,西北地区的经济极不发达,沿途除了天热时能买到几个西瓜,几乎没有东西可买。偶尔在靠近城市的地方遇到一家小店,能买到一碗清水煮面,餐桌上有一盘盐巴和一碟辣椒,就算是不错的“牙祭”。
这次黄土调查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令周镜感动的是,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全组没有任何人有怨言,各自积极完成分配的任务。他感叹说:“想想我们的艰苦只是暂时的,但那里的百姓却世代生活在那里。修好铁路,能为改善当地交通作点贡献。”
一边考察研究,周镜一边虚心向著名的黄土地质学家刘东生请教关于黄土的知识。最终,通过此次调查和试验,得到了新老黄土有不同的结构强度,阐明了各类黄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改进了基于苏联规范的黄土设计原则,为后来黄土工程性质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作为岩土工程专家,周镜的工作经常需要去到人烟罕至的地方,越是地质条件复杂、恶劣的地区,在建筑路基时越容易出问题,需要他去“问诊把脉”。周镜说:“既然从事铁路工作,就是这么个条件,既然干了这行,就要热爱它。如果不热爱自己的工作,觉得它是个包袱,你不可能绞尽脑汁地思索,很难发现问题,更难以不断提高改进,怎么也不可能干好它。”
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周镜来到西南地区,参与贵昆铁路的建设。其中,滥坝至水城段30余公里大部分要通过山间洼地的软土层,在路基修建过程中不断发生坍塌滑坡,严重影响工期。为此,贵昆铁路指挥部专门组织了科研、设计、施工三结合的战斗组,周镜作为副组长日夜奋战在工地现场。任何时候任意地方出现坍滑,他都要立刻赶赴现场,进行取样试验和研究分析,进而提出改进方案。工程后期,分别从贵阳和昆明铺过来的钢轨已完成铺设,只剩下滥水段还在紧张抢工。周镜回忆说:“那真是日日夜夜的奋斗,晚上起来都要吐。”由于长期风餐露宿,生活不规律,他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不仅时有呕吐,还有两次在工地现场出现贫血性休克,但稍事休息后仍继续坚持工作,后来,回来北京就医治疗,他因病情严重而不得不做了胃大部分切除手术。
最终,周镜成功采用多种加固软土路基措施,为贵昆铁路按时通车作出重大贡献,其中一种坡脚挡墙设计在国内外尚无先例。为此,1966年,周镜被选为铁路系统的两名科技代表之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典观礼。
“当然兴奋,但也不敢‘翘尾巴’。咱们工程就是这个特点,一定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周镜还记得,当年成功修通这条铁路,获得的唯一“犒赏”是一个写着“贵昆铁路通车纪念”的搪瓷缸子,“所有参与的人都一样。”
工程师的秘诀
贵昆铁路的工作完成后,周镜又立即转赴成昆铁路工地,担任路基战斗组副组长和锚杆战斗组组长。这条铁路沿线山势陡峭,深涧密布,沟壑纵横,穿越地质断裂带,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有“地质博物馆”之称。想在这里修建高标准的铁路,设计之难,工程之艰巨,曾令苏联专家摇头表示没有办法。
受“文革”影响,成昆铁路工程曾一度停工,周镜也一度“靠边站”。不过,最终,经过全体人员的奋战,成昆铁路于1970年7月1日建成通车。1985年,“在复杂地质险峻山区修建成昆铁路新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周镜是主要参加者之一。
除参与铁路一线工程建设外,周镜还完成了不少基于中国铁路建设实践需要的科学研究。他提出第二滑动面计算衡重式挡墙上墙土压力的原理,解决了山区铁路建设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他主持“静力触探应用技术的研究”,使静力触探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铁路工程,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参加天津塘沽新港的扩建,经唐山大地震后现场调查发现,采用他提出的软土路基加固方案的路段变形很小,该方案在新港后来的类似工程建设中被广泛采用。
改革开放后,周镜除继续参与铁路系统的科研工作外,还曾任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等职。此外,还指导了深圳机场和珠海机场的软土地基处理,参与了一些机场地基的立项评审。
他总结多年的科研经验说,工程师务必打下全面而扎实的理论基础;不能只了解工程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环节,而要掌握各个方面、所有环节的知识,并能融会贯通,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现象分析工程问题的本质;还必须培养很强的动手能力,“不能等着别人帮你完成试验,而你只会分析。”
此外,周镜格外看重的是,务必广泛阅读国内外学术文献,因为“一个人的知识毕竟很有限”。周镜在留学美国时熟练掌握了英语,回国后,国内一边倒地学苏联,他在脱产学习俄语的培训班中是优秀学生。后来发现岩土专业法国做得比较好,他就利用自己进行胃切除手术后在家休养的时间自学了法语,能够借助工具书阅读法语的学术资料。
周镜认为,工作后持续的学习非常重要,“必须跟进时代”。他一直不遗余力地了解和学习新技术,想方设法以新设备、新仪器充实自己的土工试验室。他介绍说,自己的很多工作都是缘于工程中实际问题的需要,而工作中的很多思路,都得益于日常阅读国内外文献所获得的启发。至今,他仍通过互联网随时关注专业领域内的学术最新动态。
媒体称周镜的一些学术成果“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对此,他谦虚地说:“提不了那么高,只能说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做了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推进,并不一定在理论上有很突出的创见。”
作为工程师,周镜非常注重理论和技术的创新,但他最看重的目标和最引以为豪的事始终是,“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人”
解放前,周镜的父亲曾在国民政府从事财政工作。或许缘于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切身感受,父亲教育周镜,不要从政,要有一技之长;不要靠人事关系,要靠自己的手艺生活。这个思想对周镜的影响很深。
周镜说,自己从来不是那种“有进取心”的人,从没想过要成名成家,只想如父亲所说,学门手艺,养活自己。最初,他曾考虑遵从父母的心愿学医,但听说学医要在晚上把死人骨头放在床头,随手一摸就能辨认出是哪个部位,“想想还是算了”,转而学习任何时代都需要、很容易就业的土木工程。今天回过头来看,周镜觉得自己选对了路:“做技术,最单纯,最简单。”
本来,他也没想过要出国留学,“完全没概念”,自费出国的考试是家人帮忙报的名,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轻装上阵,没想到真的考过了。到了美国,学习并不感觉到困难,从小到大学习于他而言似乎都不是难事,倒是对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印象深刻。听说有回国机会,他出于最朴素的想参与建设国家的想法递交了申请,从没想过要从中得到什么。当年,他曾任俄亥俄州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也有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邀请他参加,但他始终没有加入,因为“对政治不感兴趣”。
由于留美的经历,从“三反”、“五反”到“文革”,周镜笑称自己“在所有运动中都是运动员”。但即使经历这些波折,也从未动摇他的信念。改革开放后,他曾邀请从美国回国的同学到家里玩。他当年在美国的不少同学、朋友后来都成为了专家、教授,过着条件优裕的生活,那时,周镜尚未当选院士,国内的生活条件也还比较清苦,但他既不艳羡,也不后悔。他说:“我们苦是苦一点,但总算做了点事,在工作中解决了一些问题,得到了大家认可,这是最重要的。”
周镜喜欢自称“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人”,而不喜欢当官。在铁道建筑研究所,周镜与老搭挡卢肇钧多年分别担任土工室副、正主任,俩人合作亲密无间,双双当选院士后,还一直共用同一个办公室。周镜笑着说:“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从来不会有拉帮结派之类的事。我从来没想过把他挤掉好自己来当一把手,或者再爬爬当所长、院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
1984年,周镜“被迫”担任铁道建筑研究所所长。两年后,刚满60岁不久,他赶紧以“年满”为由主动请辞,回到土工室继续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如今,周镜已从工程一线退了下来,但仍在把握专业方向、培养人才等方面继续发挥余热。他称自己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好自己和老伴的生活。孩子不在身边,两位老人没有请保姆,一日三餐自己解决,“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
受幼年家庭教育的影响,周镜喜欢听古典音乐,还喜欢文学和历史。他说:“我活到快90岁,有一个好处,就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时代。中国现在应当可称得上是盛世,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年代能在这么长时间内没有战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我们这代人的想法,有很多看法和我们完全不同,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我很能理解。我相信,时代在进步,国家也一定在进步。对于未来,我怀有希望。”